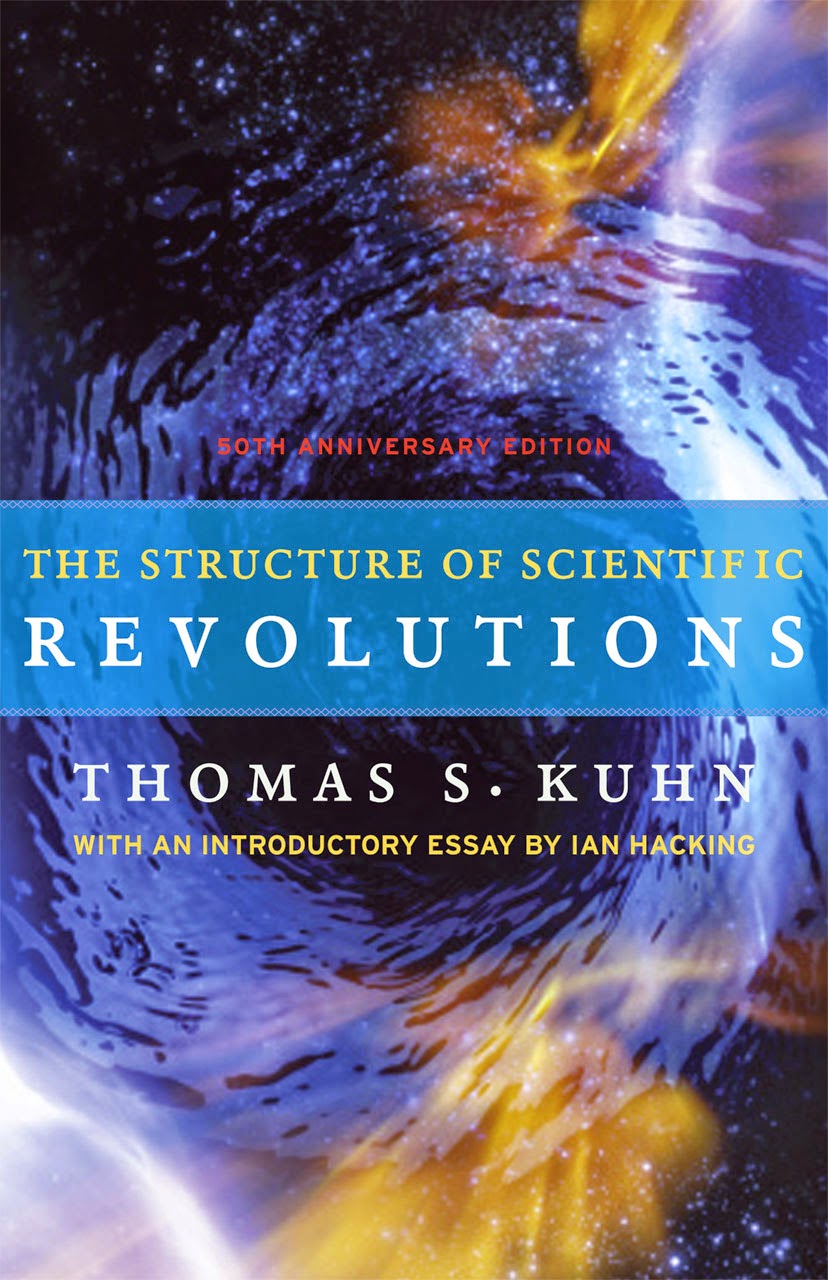先前在 Existential Comics 看了一篇探討何謂幸福的漫畫,覺得頗有深度,所以想撰文為他的論點再作一些延伸討論。
幸福是一種判斷
漫畫作者透過兩個人物的對話來帶出討論,其中一個人說所謂幸福就是 serotonin 和 dopamine ,是來自一些腦內的化學物,產生出快樂的感覺。另一個人反駁說,幸福絕不只是一種感覺而已,他提出了一個思想實驗,假想一個瘋狂科學家把你縛在椅子上,他能透過控制你腦內的化學物分泌來為你製造出最愉悅的感覺,但同時他在你面前把你的家人一個個地殺掉,這樣的情況下,你會說你幸福嗎?
當然不會!這就說明幸福不只是一種內在於我們的感覺而已,它跟我們身處的環境,以及我們對環境的詮釋有關。作者繼續舉出拿破倫以及歷史上眾多堅韌的科學家作例,指出很多超凡的偉人,都不會因自己要面對的艱辛而厭惡人生。生理上的歡悅既不是幸福的充分條件,也非其必要條件。
其實這個說法其實在心理學也可以找到它的對應,two-factor theory of emotion 就認為生理喚起(physiological arousal)要經過主體的詮釋才會成為一種情感(emotion)。這個理論跟著名的吊橋現象有關,在實驗中,心理學家讓男性受試者橫過一條吊橋,到了對岸會有一個漂亮的女實驗員派發問卷和她自己的電話號碼,讓之後對實驗有什麼疑問的受試者查詢。而控制組的受試者則不需要橫過吊橋,而是直接領取問卷和電話號碼。實驗結果發現吊橋組比控制組有更多受試者打電話給女實驗員,希望能跟她約會。這個差異很可能就是來自吊橋組的受試者錯誤地把吊橋引起的緊張感詮釋成對女實驗員的心動感覺,而他們卻完全意識不到吊橋對他們的行為有什麼影響。在這個例子中,橫過吊橋會引起受試者的一些生理喚起,例如心跳加速、冒汗、睪丸素水平提升,但受試者還需要透過他對環境的認知來尋找這些生理喚起的原因,從而詮釋出這是驚恐還是愛。
幸福這回事也很相似,它不是一種客觀的性質,而是一種判斷。判斷是由價值觀、我們對環境和自我的認知、以及我們對環境和自我的詮釋所構成的。所以家人在面前被屠殺時,縱使我的腦被注入很多 dopamine ,我還是絕不會判斷這是幸福,因為我清楚認識到家人被殺以及自己的腦內分泌受操控的事實,我也很清楚這兩個事實對我來講的意義(家人對自己的重大意義;人工製造、自我中心的愉悅感的零意義),還有我有一套價值觀,拒絕接受這種被強加的快樂。
所以,作者借角色之口作出結論︰ "Happiness is believing you are happy" 。由於幸福是一種判斷,這種判斷必定需要根據以上所講的關於事實和價值的信念(belief)作基礎。如果瘋狂科學家告訴我,家人被殺的畫面只是一個幻覺,而我又相信他,那我所受的精神困擾也會減輕很多。又,如果我信奉絕對的利己主義,認定人生的唯一目的就是快樂,那我就可能會覺得家人之死不值得讓我精神受困,倒不如好好享受科學家提供的極致歡悅。隨著人的成長,信念、認知和價值觀有所改變,我們也可能會發現以前認定為幸福的事其實很愚蠢,例如實屬虛榮幻象的名聲。所以,幸福並無其他客觀標準。一些人可以為國家為理想遭受極大的客觀痛苦卻堅持自己是幸福的,而另一些人可以在狂歡的同時感到空虛寂寞,生命了無意義;這些差異都是跟不同人的不同信念,或同一個人在不同時空下的不同信念有關。
自欺與絕望
這個年頭講「信念」,很容易就會聯想起一種「正能量」式的自欺欺人--我只要把自己所面對的所有事都詮釋成好事,或者把所有問題都塞進床底下,那不就沒有煩惱了嗎?這不是不行,但卻有一種危險︰當事情演變到我們無法不作正視的時候,我們就已經無可能挽回了。對 Leo Tolstoy 來說,迫使我們誠實地反思人生的最後一道王牌,就是死亡。他的短篇 The Death of Ivan Illyich 談的就是一個典型的公務員 Ivan ,他以追隨上流社會的生活風尚來引導自己的人生,所以他跟所有人一樣,娶了一個體面的老婆,生了幾個小孩。但有家庭就注定有麻煩,他不想因為家庭而失去他的心境安寧,所以他的解決之道就是借工作為藉口逃避家人。妻子和孩子們抱怨愈多,他對工作就愈投入。這種對工作的投入,也為他贏來他想要的財富和地位,他對一切都非常滿意,人生沒有比這樣更好了。可是,一天他發現了自己患上了不明之症,他的身體告訴他將命不久已,他開始對死亡的未知惶恐起來,卻發現身邊沒有任何人願意分擔他的焦慮。 Ivan 在面對死亡的這幾個月內感到無比孤獨,家人對他因痛苦而發的嚎哭也漸漸變得習以為常, 沒有人願意真的投入到一個瀕死者的內心,更多人為了維持日常生活運轉而假裝他沒有事,職場上認識的人把工作看得重,都不會關心他,而家人的關係本身已很疏離,現在更成了他們的負擔。比起肉體上的痛苦,精神上的痛苦更讓他崩潰。 Ivan 於是被迫思考,究竟是什麼出了錯,讓他那個愜意的人生,會以如此孤獨不安的方式結束?他拼命地回憶,想要搞清楚,而直接臨終的那一天,他才醒悟︰「啊,那種所謂上流社會的生活風尚,會不會其實是錯誤的?」那些表面幸福的在上位者,會不會也是在臨死前才被迫償還借來的快活,才發現自己的錯誤,但那時已經沒有一個人可以傾訴?就在這瀕死的一刻, Ivan 的信念全數被推翻,他發現自己的整個人生都是一場錯誤,但他已經沒有改正的機會了,於是他只好在絕望與孤獨之中死去。
自欺欺人和鴕鳥政策的代價,就是臨終的絕望。
The Death of Ivan Illyich 這則寓言,不能僅當作是 Tolstoy 對上流社會的批判。習染上流社會的市儈俗氣,固然是 Ivan 最後要面對如此強烈的虛無感的原因之一,但即使假設 Ivan 是一個有理想熱血的人,追逐的不是上流社會,而是以傑出運動員為榜樣,一生在體育界上攀爬,會否也有一日因為疾病或其他原因,而後悔他為理想犧牲了跟家人和朋友相處的時間?會不會後悔他所放棄了的青春?又如果他能做到面面俱圓,會不會也有可能最終後悔自己一生平庸,沒有發揮自己的極限?我們總會覺得「不會的,我對自己的生活方式很有信心,我不會後悔的」,但這有可能中了一個認知偏差(cognitive bias)的陷阱︰我們總會高估了自己性情和思想的 constancy ,例如我們會覺得十年後的自己跟現在不會差異很大,但當去回想十年前的自己是如何時,又發現十年間自己變化很大。這就是我們的存在困境︰幸福建立於信念之上,而信念又很容易被推翻。除了我們的性情和價值觀會因時間改變而推翻先前的信念,一些 life events ,例如疾病、死亡、中年危機或原有的生活慣性因突如其來的改變(產子、離婚、失業、家人逝世等)而被打亂,也會令我們不得不反思人生,重新尋找意義。困難就在於,我們很難預測到怎樣才是一個無悔的人生。
自由的代價
存在主義哲學家 Søren Kierkegaard 會說︰無論你如何選擇自己的人生,你也會後悔。一位朋友因不知道應否跟一個女子結婚,於是寫信向 Kierkegaard 請求意見(他真是問對人了), Kierkegaard 如此回應︰
I see it all perfectly; there are two possible situations — one can either do this or that. My honest opinion and my friendly advice is this: do it or do not do it — you will regret both. [1]無論你做還是不做,你都會後悔。如果你為了理想而犧牲家庭,當你年老患病最需要家人時卻無法再彌補跟子女的情感疏落,你就會後侮;如果你為了家庭而犧牲理想,當你人生已過一大半時,你又會不甘自己的平庸,你會厭惡不斷重複的日常,你會變得忌恨年青人,你會後悔沒有貫徹理想。 Kierkegaard 說,所謂的畏懼(dread),就是意識到自己有可能亦有自由去進行選擇。正因為我們有自由去選擇自己要追逐理想與否,我們就要對其後果負上責任。意識到自己要為每一個決定負責,這種負擔能使人窒息,遲遲不敢作決定。
我們對自己的信念感到不確定,這個不確定性除了是外在的(我們所不能操控的際遇和運氣),也是內在的,即我們意識到在我們選擇的信念之外,有無限多的其他可能,我們無法避免懷疑自己的選擇是否較好的。所以,要幸福的話,只有信念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把信念轉化為信仰。我們可以把「信仰」(faith)定義為「可能性的持續廢除(continuous annullation of possibilities)」。認定一個人生信仰,例如我要當一個運動員,就要持續地去廢除其他存在的可能性︰我有做個工資可觀的白領的可能;我有成為體育老師,換取安穩生活的可能;我有放棄自己本來的計劃,跟隨被調職的丈夫到外國生活的可能。把一種偶然之下獲取的想法,一種在某個時刻機緣巧合下產生的熱情,一種受成長環境灌輸的價值觀,認定為是必然的,不可更改的,必須服從的人生志業,這就是信仰。所以,宗教是一種信仰,如果我不是生長於基督教家庭而是生長於伊斯蘭教家庭,我就不會信奉基督教,但我既然已經信奉基督教,我要不被這種信念的任意性(arbitrariness)所動搖,我就要把這種偶然認定為必然,把信念化為信仰。[2]愛情也是一種信仰,所謂愛情就是把一個偶然遇到,實際上並非唯一的對象視為唯一。如果我們不持續廢除「我這個伴偶隨時可以由其他人代替」的可能性,我們就無法專一,無法維持任何長久關係。[3]其他的事上,如事業的決定、政治上的抉擇、道德上的選擇,都或多或少依循這個邏輯︰如果我們時刻不忘自己的政治取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階級背景、自己所接觸的有限資訊以及種種偶然因素所產生的偏見,那我們就很難在政治上有任何行動。[4]
Fyodor Dostoevsky 所著的 Notes from Underground 正正是描寫這樣的一個人物,他經常懷疑自己,生怕被自己的大腦所騙,他無法形成任何持久的信念,更不用說有任何信仰,他認為那些能在生活中很主動(active)的人,都是因為不夠清醒(less conscious)和不夠聰明(less intelligent),那些人正是因為不知道如何批判自己、分析自己,才會那麼幼稚地把很多事情視為理所當然。但如此高傲的他卻因自己的懷疑主義而無法投入生活,常為自己失敗的人生感到羞恥。 Dostoevsky 寫這本書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批判理性主義對傳統信仰的侵蝕,如果每一種實踐(practice)都要求一個理性的辯護(rational justification),那我們最終會發現每一個辯護理由都有合理化(rationalisation)的可疑[5],於是會喪失任何行動的起點,循入虛無主義。傳統和宗教的社會功能就在於給予個人一個既定角色和意義網絡,例如作為新教徒,我的存在意義就是以辛勤的工作來榮耀上帝,無論如何我也不去審問這個教條的基礎,我就能安心地以這個標準來判斷自己的人生成功與否,而不需要因對標準本身產生懷疑而懷疑自己的幸福。有了信仰,我就起碼能有一條通往幸福的路線圖,接下來就是努力向著一個特定終點前進,不為其他可能終點而分心。
可是,正如 Jean-Paul Sartre 指出,接受什麼宗教信仰的指引,歸根究底都是個人自由的選擇,我們無法把責任推卸給教會、家庭或政黨,所以還是要回到那個核心問題︰我們應該如何作出選擇?其實人生信仰的選擇根本沒有理性基礎可言,我們無論怎樣思考都無法有一個確鑿的答案,固此也沒有什麼根據可以讓我們肯定的說「這就是幸福。」最普遍的對策是,乾脆假裝幸福不是一種判斷,而是一種感覺︰既然一切都不確定,既然一切都轉眼即逝,既然幹什麼都會後悔,那為什麼不把握當下的快樂,聽任情緒的指揮呢?--諸君,繞了一大個圈,我們還是回到了我們當代的時代精神。
[1]Either/Or: A Fragment of Life; my italic.
[2]參考拙文︰G. A. Cohen 與哲學信念
[3]關於把偶然化作必然的這一點,跟 Friedrich Nietzsche 的「永劫回歸」(eternal recurrence)也有關係,Milan Kundera 在小說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中對這一點作出了非常精彩的詮釋。
[4]參考拙文︰不惑之年
[5]Nietzsche 在 Beyond Good and Evil 和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 中剖析了自古以來道德原則的辯護如何其實是一種合理化,筆者的懷疑主義也是受其影響。
延伸閱讀︰
拙文〈不惑之年〉
拙文〈G. A. Cohen 與哲學信念〉
Existential Comics: Two Brothers
漫畫 Supernormal Stimuli: This is Your Brain on Porn, Junk Food, and the Internet
清哲學︰〈海德格與托爾斯泰〉
Social Psychology, Elliot Aronson et al.
The Death of Ivan Illyich, Leo Tolstoy
A Confession, Leo Tolstoy (Introduction)
Notes from Underground, Fyodor Dostoevsky
Crime and Punishment, Fyodor Dostoevsky
Existentialism is a Humanism, Jean-Paul Sartre
The Age of Reason, Jean-Paul Sartre
Either/Or: A Fragment of Life, Søren Kierkegaard
Beyond Good and Evil, Friedrich Nietzsche
Liquid Modernity, Zygmunt Bauman
電影︰
楊德昌《海灘的一天》、《一一》
Ingmar Bergman: Wild Strawberry; Winter Light; Autumn Sonata
Paul Thomas Anderson: Magnolia
Mike Leigh: Naked